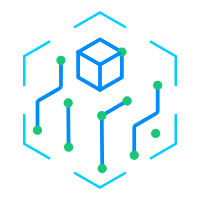爱科农郭建明:搞数字化种植科学家也得先证明自己会种地
爱科农郭建明:搞数字化种植科学家也得先证明自己会种地
爱科农郭建明:搞数字化种植科学家也得先证明自己会种地,现代农业科技视频,农业知识种植小科普,《农业科学》,
说到农业,种地十几年的老赖皱了皱眉。这位80后年轻人(如果还算的话)在老家黔西南地区种过水果、茶叶、中草药,也搞过农业咨询服务,做过或接触过农业的方方面面,从农资到土地流转,从种植到管理,再到打造农产品品牌,操盘项目融资,无一不干。如果有需要,他可以在三五天内做出一份漂亮的农业项目全产业链可研报告。然而十几年来,他败多胜少,最后黯然退出,发誓再也不碰这个行当。
老赖在当地小有名气,农户遇到问题,总是想起这位在土地里成长起来的“专家”。老赖有求必应,到处为人出谋划策,最多时,同时在十余家农企、合作社兼职,疲于奔命。他曾寄希望于互联网,相信数据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,坚称不仅仅是在流通和品牌方面,种植方面,数据亦有用武之地,奈何自己能力不足,空有想法,难以付诸实践。说到这里,他撇了撇嘴,欲言又止。“我还是想看看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后,会发生什么。”这位执着的全产业链玩家决定说出内心的期望。
农业产业数字化最早开始于流通和消费端,互联网部分改变了农产品供需匹配方式,随后进入到上游农资领域。随着农业自动化的发展,加上计算机技术、遥感技术、GPS和物联网等方面的进步,智能农机具开始出现并不断提高“智力”表现。最后进入数字化视野的是种植,在这个综合了地理学、生态学、土壤学和植物生理学等诸多基础学科,同时又夹杂着大量效果难辨的个人经验和民间智慧的领域,数字化难度最高,发展最为缓慢,但近些年仍不乏勇猛之士,高举“数据和算法”大旗,践行“软件先行”的理念,投身其中。
一群农业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家组建了一家叫爱科农的数字农业公司,开发了一套智慧种植决策系统,专注粮食作物的科学种植,简单而言,这套系统经过算法校准及模型优化,可以得出一些结论,告诉农民该种什么,怎么种,何时浇水施肥、用药,用量多少,几乎涵盖了种植的方方面面。踌躇满志的科学家跑到农村,向农户推广自己的得意之作,声称可以帮助后者提高产量,降低成本。农户也不简单,表示如果科学家们可以在种地方面胜过自己,可以考虑使用他们的方案,并付一些费用。
郭建明觉得农户的要求合情合理。郭建明是爱科农的创始人兼CEO,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,曾任中种国际副总裁。郭建明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不属于那种夸夸其谈、墨守陈规的学术派,当农户提出挑战时,郭懂得变通,在全国,目前主要是北方几大粮食主产区开辟了10万亩自营示范田,用自家的智慧种植决策系统做指导,将毛利从15%的平均值提升到30%。农民简单务实,见效后纷纷加入。
爱科农的创始团队也不属于那种执着于“创造价值就一定能挣钱”的理想主义者,他们不会羞于谈论挣钱,对企业的生存问题重视有加。尽管爱科农起初设定的目标是做一个SaaS公司,想着做成本低,毛利高,关系简单的生意,但当SaaS模式难以迅速打开局面时,他们选择从种植户无法避开的农资,当然是围绕模型、算法和数据的优势开展,并尊重现存的产业规则,不与传统的农资经销商争利,而是加强合作,奉行互惠互利的原则。成立仅仅6年,爱科农已经实现年收过亿元。“商业模式基本跑通了,接下来不会盲目扩充新的收入来源,而是在现有模式上做大收入规模。”郭建明说。
郭建明懂得克制,相较于将业务延展到上游农资生产和下游品牌建设(熟悉的全产业链玩法),郭建明强调种植端仍然有许多事情可以做,帮助老百姓种植仍然是公司的焦点所在。因此一切仍是回归到模型、算法、数据,以及下地干活。
第一类是无人机植保,在种植过程中起到防治病虫害的作用,借助一些数字化技术,比如光谱分析,可以研究出一块地的受灾严重程度,相应地采取措施,让农药喷洒的效率更高。另外,在南方山区、丘陵地带,这些大型农机进不去的地方,采用无人机就非常方便。
第二类是传感器,通过在田间插一些物联网设备,可以获得比如空气中温度、湿度、土壤含水量等数据。第三类是水肥一体化,通过设备和技术,提高肥料和水的使用效率,对农田进行高效的管理。还有一类是智能农机,有前装后装,不展开讲。
但是整体上讲,这些方面帮农民解决了一些问题,但没有照顾到农业种植现存的一些实际问题。举个例子,在田里插传感器,获得了一些数据,但是农民或者农场、合作社没有办法来判断并使用这些数据。
问:爱科农看到了行业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挑战和不足,所以选择从这个方面切入?
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逻辑。我们看美国,The Climate Corporation这家公司是农业数字化的鼻祖了,它的主要能力集中在算法和研发上面。然后跟约翰迪尔这样的传感器公司合作,数据共享,对数据处理后,提供给农场或者种植公司,告诉他们如何在田间进行科学种植。
那回到中国,其实我们也可以。但是又有些不同,举个例子,美国的一个现代化农场,平均有50个传感器,中国大部分农场没有传感器。我们国家获取数据的难度较高,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,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,比如采用气象差值计算,用来弥补数据量偏小的问题。
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。中国的农业种植数字化会经历几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没有任何的田间数据,跑去农民家里问你家地里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多少,PH值多少,我相信99%的农民回答不上来;第二阶段,我们没有办法把传感器一下子插到老百姓田里去,因为成本太高了,老百姓一亩地挣300块钱,你让他花几千几万块钱装传感器不现实。那在这个阶段,我们通过算法的手段,利用地方气象站的数据,部分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,把地块未来生长季内的所需数据计算出来,虽然这跟完全有传感器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会有差距,但相比以往没有基础数据,是一个很大的进步,而且可以输出比原来更科学的种植方法;再往后发展,就是老百姓发现这些科学种植方法真的对他帮助很大,那他可能接受在田间插传感器,而且密度不用很高,这样我们得到的数据会更加精准,计算的结果也更加精准。
目前我们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第一阶段,我们正在往第二阶段做,中国18亿亩耕地,我们只服务了几千万亩。
问:相对来说,规模种植地区的环境数据对地块数据的参考性更准确,所以你们选择规模种植地区的大规模粮食种植户为主要客户?
是的。这取决于两方面,一方面规模种植户对新技术带来的投入产出比是非常在意的。要是在我老家,平均一户就3亩地,如果这个新技术让一亩地多挣100块钱,在我老家就只能挣300,挣得太少了,大家就不太想要听你讲怎么用,怎么实践,万一他哪个步骤搞错了,回头还找技术人员,太麻烦了。那么新疆一户可能是1000亩,那就不同了,能多挣10万块,还是有兴趣了解新技术是怎么回事。二方面,如果未来要进入到第三阶段,他因为经历过第二阶段,意识到了数据的重要性,他可以算账,比如1000亩地加一套传感器是2万块钱,那平均到每亩也就20块。但对于3亩地来说,一套2万块的传感器就很贵了。
所以我认为农业种植的数字化进程,当下规模种植户或者合作社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对象。在地域上,北方比南方更适合。
一个是和农机具的配合,比如按照我们数据推演,一亩地最好是种4500株玉米,虽然播种机是按照这个数字种的,但是发芽的时候发现有些就不太好,因为播种机不给力,种得深浅不一,甚至漏种。那么这就会反作用给农机具的制造商,提高技术标准,提高种植效率,好的农机具反过来又可以印证数字化技术的科学种植决策效果。
一个是农资方面。数字化工具出来之前,对于某一地种什么品种,多大密度,病虫害防治,往往靠的是经验。比如按照往年经验,某一地就应该种B品种,但我们通过算法得出的结论是A品种,我们把结论告诉农户,帮助增产。用药也是,当你发现地里作物长虫了,但很小,觉得可以不打,但是等虫长大了,再用药控制不住,就成倍增加用量,然后怀疑是不是药不行,其实用数据一分析,就是时机不对。就这部分来说,那数字化工具的作用就是告诉你何时用药,用多大量。数字化工具和农资的关系,有点像药方和药的关系,就是你有好的药方,但没有好的药,达不到效果;有好的药没有好的药方,不知道怎么用,也没效果。
目前我们主要是为种植户提供种植建议,不会强制要求买什么设备或农资,平台上也没这样的服务。但我们会提供一些农资定制服务。我们还是尽可能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提供科学的种植建议,实现最优水平。当然我们想要带着农民一起干数字化种植这个事情,农民说你的这个数据有用,你的农资配方好,但是我没有用过,也不敢用,你能不能做一个示范,我看到效果之后再用。
是的。假如说一开始我们去农村,跟别人说我们是孟山都出来的,中科院出来的,我们发明了一套算法,可以帮你节约多少成本,提高多少产量,你愿不愿意用,付点费用,我估计老百姓会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,说你们这帮人种过地吗?我在这个地方种了20年,我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,除非你种得比我好。所以我们就做示范田,他们慢慢地看到了效果,才愿意跟我们合作。所以这个示范田是我们的业务推广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有的。我们说示范田一共有四个方面的作用。一是因为我们的员工在现场进行管理,可以采集真实的数据;二是可以优化我们的模型和种植决策,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示范田,可以比较灵活地试验;三是推广示范的作用;四是既然要证明我的方法好,那我肯定要比农民挣得多,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是盈利的,是我们公司的收入来源之一了。我们认为吃饭的问题很重要。
我看到网络上,农业这方面的毛利一般是15%,我们可以做到30%以上。我们觉得谈钱并不可耻,你说一帮科学家,在地里不挣钱的话,你把技术介绍给农民,农民更不挣钱,那你的技术没用啊,所以我们必须要展示我们的技术能在地里真真正正的挣到钱。
我们主要是种玉米,在黑龙江、内蒙、新疆、宁夏、甘肃和湖北都有基地。另外,在山东做了一些小麦的示范地,在内蒙有马铃薯的示范地,在上海和黑龙江有水稻的示范地。
自营的有10万亩,还有一些合作的。自营就是资金、技术、种植管理都是我们自己做,包括土地流转,农资投入。合作的话我们出人出技术,合作伙伴拿钱拿地,我们用技术帮助他种。一个一万亩的项目,一般1个技术人员就够了,但我们会派2个。
然后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,收费不一样,比如说,只用APP的,我们就收SaaS费,一亩地10块钱,如果要派人过去,一亩地就是20块钱,如果从头到尾都需要我们的人驻场,一亩地收100,这个看合作伙伴的能力和需求。
问:反正不管是哪种方式,背后主要用的还是你们的模型和数据?那么在数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,你们如何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,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呢?
是的。刚刚也谈到了数据,我们的数据一共有4个来源。一是中国气象局,我们从一些官方授权的下属企业进行合作,经过气象差值计算后推算到每个地块上,并应用到模型当中,这是气象数据;土壤数据主要来自于两块,一是国家权威机构,比如中科院、农科院有一些公开数据,另一块是我们在辽宁有一个土壤实验室,服务的地块我们会取一些土壤样本进行测试,这构成了我们土壤的基础数据库;第三块是卫星和无人机的遥感数据,卫星数据主要是国内外的一些公开数据,无人机这一块我们有自采,也有合作伙伴;第四块是品种生育期数据,我们和一些大型的公司合作,把数据参数化之后用到我们的模型里面。未来我们也积极寻求拥有数据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合作,尽可能补充。
我们做的是一套白箱模型的算法,是基于机理模型,这就决定了我们无需那么多的数据,只需要少量的但是非常精准的数据,可以把算法做到非常精准。举个例子,比如某一种作物,每长出一片叶子需要50度的积温,那么通过算法算出来,不管南方北方,只要积温达到就可以长出一片叶。所以我们也不是非得大规模采集数据,而是要采集符合我们算法需求的数据。
问:爱科农介入农资行业,是因为你本人在中种国际和孟山都的一些经验优势,还是市场上出现了新需求?
一开始我们做这个公司的时候,我们要做的是SaaS,因为这个东西很轻,尤其是产品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成本很低,毛利很高,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是刚刚也说到了,单单卖一个SaaS很难,农民不买账。那么我们在做示范地的时候,我们在智慧种植决策系统的决策下,建议使用一些特定的农资。老百姓看到了说没见过,也买不到,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,农民一开始不会买你的服务,但会买你的农资,但是他们又凑不齐一个大单,厂家也不会给他们定制,所以我们就想收集这样的需求,凑齐了以后找厂家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把农资和技术用到他的地里去,把农资里面的一些利润作为技术的转化费用,这件事对农民来说比较容易接受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我们开始通过数字化工具帮助农民定制最适合他们的农资,确保他们的地块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收益。
而且农资的市场天花板非常高,整个农资市场高达3万亿,定制化的可能占一半,哪怕10%的毛利,真的太大了。
其实我们没有直接卖给农户任何农资,我们是找了一些农资经销商,让他们把农资带给农户。一开始我们找了一些对科技非常感兴趣的农资经销商,告诉他们可以用数字工具帮助他们服务好终端客户(农户),因为经销商以前都是拼价格,现在当你有了一个工具更好的服务客户,他们获得更好的产量和收益后,自然会买更多的农资,那在这个过程中,经销商就会收集农户的土地信息,这些信息给我们之后,我们通过模型算法计算,得出一些农资方面的决策,经销商再问农户要不要,如果要那就交订金,这个量攒到一定规模后,我们可以到市面上找一家厂商定制出来,再由经销商卖给农户,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
是的。有些客户用了我们的技术,收益变高了,他想扩产,但是缺乏资金支持,找到我们寻求帮助,我们因为合作过,对他的地块数据表现很清楚,知道这个人非常可靠,就想帮助他们,慢慢接入了一些金融产品进来。
因为农业金融比较难做,主要是缺乏数据,金融机构没办法详细了解农户的地块种植情况、产量以及历史经营情况,那我们可以帮农户做一个信用报告,供金融机构参考。
不过,金融在我们的收入中占的比例非常小,我们投入的精力很小。目前,我认为在种植端能做的事情非常多,还是要聚焦在帮助老百姓种好地。
说到农业,种地十几年的老赖皱了皱眉。这位80后年轻人(如果还算的话)在老家黔西南地区种过水果、茶叶、中草药,也搞过农业咨询服务,做过或接触过农业的方方面面,从农资到土地流转,从种植到管理,再到打造农产品品牌,操盘项目融资,无一不干。如果有需要,他可以在三五天内做出一份漂亮的农业项目全产业链可研报告。然而十几年来,他败多胜少,最后黯然退出,发誓再也不碰这个行当。老赖在当地小有名气,农户遇到问题,总是想起这位在土地里成长起来的“专家”。老赖有求必应,到处为人出谋划策,最多时,同时在十余家农企、合作社兼职,疲于奔命。他曾寄希望于互联网,相信数据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,坚称不仅仅是在流通和品牌方面,种植方面,数据亦有用武之地,奈何自己能力不足,空有想法,难以付诸实践。说到这里,他撇了撇嘴,欲言又止。“我还是想看看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后,会发生什么。”这位执着的全产业链玩家决定说出内心的期望。
农业产业数字化最早开始于流通和消费端,互联网部分改变了农产品供需匹配方式,随后进入到上游农资领域。随着农业自动化的发展,加上计算机技术、遥感技术、GPS和物联网等方面的进步,智能农机具开始出现并不断提高“智力”表现。最后进入数字化视野的是种植,在这个综合了地理学、生态学、土壤学和植物生理学等诸多基础学科,同时又夹杂着大量效果难辨的个人经验和民间智慧的领域,数字化难度最高,发展最为缓慢,但近些年仍不乏勇猛之士,高举“数据和算法”大旗,践行“软件先行”的理念,投身其中。
一群农业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家组建了一家叫爱科农的数字农业公司,开发了一套智慧种植决策系统,专注粮食作物的科学种植,简单而言,这套系统经过算法校准及模型优化,可以得出一些结论,告诉农民该种什么,怎么种,何时浇水施肥、用药,用量多少,几乎涵盖了种植的方方面面。踌躇满志的科学家跑到农村,向农户推广自己的得意之作,声称可以帮助后者提高产量,降低成本。农户也不简单,表示如果科学家们可以在种地方面胜过自己,可以考虑使用他们的方案,并付一些费用。
郭建明觉得农户的要求合情合理。郭建明是爱科农的创始人兼CEO,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,曾任中种国际副总裁。郭建明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不属于那种夸夸其谈、墨守陈规的学术派,当农户提出挑战时,郭懂得变通,在全国,目前主要是北方几大粮食主产区开辟了10万亩自营示范田,用自家的智慧种植决策系统做指导,将毛利从15%的平均值提升到30%。农民简单务实,见效后纷纷加入。
爱科农的创始团队也不属于那种执着于“创造价值就一定能挣钱”的理想主义者,他们不会羞于谈论挣钱,对企业的生存问题重视有加。尽管爱科农起初设定的目标是做一个SaaS公司,想着做成本低,毛利高,关系简单的生意,但当SaaS模式难以迅速打开局面时,他们选择从种植户无法避开的农资,当然是围绕模型、算法和数据的优势开展,并尊重现存的产业规则,不与传统的农资经销商争利,而是加强合作,奉行互惠互利的原则。成立仅仅6年,爱科农已经实现年收过亿元。“商业模式基本跑通了,接下来不会盲目扩充新的收入来源,而是在现有模式上做大收入规模。”郭建明说。
郭建明懂得克制,相较于将业务延展到上游农资生产和下游品牌建设(熟悉的全产业链玩法),郭建明强调种植端仍然有许多事情可以做,帮助老百姓种植仍然是公司的焦点所在。因此一切仍是回归到模型、算法、数据,以及下地干活。
第一类是无人机植保,在种植过程中起到防治病虫害的作用,借助一些数字化技术,比如光谱分析,可以研究出一块地的受灾严重程度,相应地采取措施,让农药喷洒的效率更高。另外,在南方山区、丘陵地带,这些大型农机进不去的地方,采用无人机就非常方便。
第二类是传感器,通过在田间插一些物联网设备,可以获得比如空气中温度、湿度、土壤含水量等数据。第三类是水肥一体化,通过设备和技术,提高肥料和水的使用效率,对农田进行高效的管理。还有一类是智能农机,有前装后装,不展开讲。
但是整体上讲,这些方面帮农民解决了一些问题,但没有照顾到农业种植现存的一些实际问题。举个例子,在田里插传感器,获得了一些数据,但是农民或者农场、合作社没有办法来判断并使用这些数据。
问:爱科农看到了行业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挑战和不足,所以选择从这个方面切入?
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逻辑。我们看美国,The Climate Corporation这家公司是农业数字化的鼻祖了,它的主要能力集中在算法和研发上面。然后跟约翰迪尔这样的传感器公司合作,数据共享,对数据处理后,提供给农场或者种植公司,告诉他们如何在田间进行科学种植。
那回到中国,其实我们也可以。但是又有些不同,举个例子,美国的一个现代化农场,平均有50个传感器,中国大部分农场没有传感器。我们国家获取数据的难度较高,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,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,比如采用气象差值计算,用来弥补数据量偏小的问题。
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。中国的农业种植数字化会经历几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没有任何的田间数据,跑去农民家里问你家地里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多少,PH值多少,我相信99%的农民回答不上来;第二阶段,我们没有办法把传感器一下子插到老百姓田里去,因为成本太高了,老百姓一亩地挣300块钱,你让他花几千几万块钱装传感器不现实。那在这个阶段,我们通过算法的手段,利用地方气象站的数据,部分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,把地块未来生长季内的所需数据计算出来,虽然这跟完全有传感器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会有差距,但相比以往没有基础数据,是一个很大的进步,而且可以输出比原来更科学的种植方法;再往后发展,就是老百姓发现这些科学种植方法真的对他帮助很大,那他可能接受在田间插传感器,而且密度不用很高,这样我们得到的数据会更加精准,计算的结果也更加精准。
目前我们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第一阶段,我们正在往第二阶段做,中国18亿亩耕地,我们只服务了几千万亩。
问:相对来说,规模种植地区的环境数据对地块数据的参考性更准确,所以你们选择规模种植地区的大规模粮食种植户为主要客户?
是的。这取决于两方面,一方面规模种植户对新技术带来的投入产出比是非常在意的。要是在我老家,平均一户就3亩地,如果这个新技术让一亩地多挣100块钱,在我老家就只能挣300,挣得太少了,大家就不太想要听你讲怎么用,怎么实践,万一他哪个步骤搞错了,回头还找技术人员,太麻烦了。那么新疆一户可能是1000亩,那就不同了,能多挣10万块,还是有兴趣了解新技术是怎么回事。二方面,如果未来要进入到第三阶段,他因为经历过第二阶段,意识到了数据的重要性,他可以算账,比如1000亩地加一套传感器是2万块钱,那平均到每亩也就20块。但对于3亩地来说,一套2万块的传感器就很贵了。
所以我认为农业种植的数字化进程,当下规模种植户或者合作社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对象。在地域上,北方比南方更适合。
一个是和农机具的配合,比如按照我们数据推演,一亩地最好是种4500株玉米,虽然播种机是按照这个数字种的,但是发芽的时候发现有些就不太好,因为播种机不给力,种得深浅不一,甚至漏种。那么这就会反作用给农机具的制造商,提高技术标准,提高种植效率,好的农机具反过来又可以印证数字化技术的科学种植决策效果。
一个是农资方面。数字化工具出来之前,对于某一地种什么品种,多大密度,病虫害防治,往往靠的是经验。比如按照往年经验,某一地就应该种B品种,但我们通过算法得出的结论是A品种,我们把结论告诉农户,帮助增产。用药也是,当你发现地里作物长虫了,但很小,觉得可以不打,但是等虫长大了,再用药控制不住,就成倍增加用量,然后怀疑是不是药不行,其实用数据一分析,就是时机不对。就这部分来说,那数字化工具的作用就是告诉你何时用药,用多大量。数字化工具和农资的关系,有点像药方和药的关系,就是你有好的药方,但没有好的药,达不到效果;有好的药没有好的药方,不知道怎么用,也没效果。
目前我们主要是为种植户提供种植建议,不会强制要求买什么设备或农资,平台上也没这样的服务。但我们会提供一些农资定制服务。我们还是尽可能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提供科学的种植建议,实现最优水平。当然我们想要带着农民一起干数字化种植这个事情,农民说你的这个数据有用,你的农资配方好,但是我没有用过,也不敢用,你能不能做一个示范,我看到效果之后再用。
是的。假如说一开始我们去农村,跟别人说我们是孟山都出来的,中科院出来的,我们发明了一套算法,可以帮你节约多少成本,提高多少产量,你愿不愿意用,付点费用,我估计老百姓会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,说你们这帮人种过地吗?我在这个地方种了20年,我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,除非你种得比我好。所以我们就做示范田,他们慢慢地看到了效果,才愿意跟我们合作。所以这个示范田是我们的业务推广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有的。我们说示范田一共有四个方面的作用。一是因为我们的员工在现场进行管理,可以采集真实的数据;二是可以优化我们的模型和种植决策,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示范田,可以比较灵活地试验;三是推广示范的作用;四是既然要证明我的方法好,那我肯定要比农民挣得多,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是盈利的,是我们公司的收入来源之一了。我们认为吃饭的问题很重要。
我看到网络上,农业这方面的毛利一般是15%,我们可以做到30%以上。我们觉得谈钱并不可耻,你说一帮科学家,在地里不挣钱的话,你把技术介绍给农民,农民更不挣钱,那你的技术没用啊,所以我们必须要展示我们的技术能在地里真真正正的挣到钱。
我们主要是种玉米,在黑龙江、内蒙、新疆、宁夏、甘肃和湖北都有基地。另外,在山东做了一些小麦的示范地,在内蒙有马铃薯的示范地,在上海和黑龙江有水稻的示范地。
自营的有10万亩,还有一些合作的。自营就是资金、技术、种植管理都是我们自己做,包括土地流转,农资投入。合作的话我们出人出技术,合作伙伴拿钱拿地,我们用技术帮助他种。一个一万亩的项目,一般1个技术人员就够了,但我们会派2个。
然后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,收费不一样,比如说,只用APP的,我们就收SaaS费,一亩地10块钱,如果要派人过去,一亩地就是20块钱,如果从头到尾都需要我们的人驻场,一亩地收100,这个看合作伙伴的能力和需求。
问:反正不管是哪种方式,背后主要用的还是你们的模型和数据?那么在数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,你们如何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,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呢?
是的。刚刚也谈到了数据,我们的数据一共有4个来源。一是中国气象局,我们从一些官方授权的下属企业进行合作,经过气象差值计算后推算到每个地块上,并应用到模型当中,这是气象数据;土壤数据主要来自于两块,一是国家权威机构,比如中科院、农科院有一些公开数据,另一块是我们在辽宁有一个土壤实验室,服务的地块我们会取一些土壤样本进行测试,这构成了我们土壤的基础数据库;第三块是卫星和无人机的遥感数据,卫星数据主要是国内外的一些公开数据,无人机这一块我们有自采,也有合作伙伴;第四块是品种生育期数据,我们和一些大型的公司合作,把数据参数化之后用到我们的模型里面。未来我们也积极寻求拥有数据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合作,尽可能补充。
我们做的是一套白箱模型的算法,是基于机理模型,这就决定了我们无需那么多的数据,只需要少量的但是非常精准的数据,可以把算法做到非常精准。举个例子,比如某一种作物,每长出一片叶子需要50度的积温,那么通过算法算出来,不管南方北方,只要积温达到就可以长出一片叶。所以我们也不是非得大规模采集数据,而是要采集符合我们算法需求的数据。
问:爱科农介入农资行业,是因为你本人在中种国际和孟山都的一些经验优势,还是市场上出现了新需求?
一开始我们做这个公司的时候,我们要做的是SaaS,因为这个东西很轻,尤其是产品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成本很低,毛利很高,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是刚刚也说到了,单单卖一个SaaS很难,农民不买账。那么我们在做示范地的时候,我们在智慧种植决策系统的决策下,建议使用一些特定的农资。老百姓看到了说没见过,也买不到,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,农民一开始不会买你的服务,但会买你的农资,但是他们又凑不齐一个大单,厂家也不会给他们定制,所以我们就想收集这样的需求,凑齐了以后找厂家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把农资和技术用到他的地里去,把农资里面的一些利润作为技术的转化费用,这件事对农民来说比较容易接受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我们开始通过数字化工具帮助农民定制最适合他们的农资,确保他们的地块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收益。
而且农资的市场天花板非常高,整个农资市场高达3万亿,定制化的可能占一半,哪怕10%的毛利,真的太大了。
其实我们没有直接卖给农户任何农资,我们是找了一些农资经销商,让他们把农资带给农户。一开始我们找了一些对科技非常感兴趣的农资经销商,告诉他们可以用数字工具帮助他们服务好终端客户(农户),因为经销商以前都是拼价格,现在当你有了一个工具更好的服务客户,他们获得更好的产量和收益后,自然会买更多的农资,那在这个过程中,经销商就会收集农户的土地信息,这些信息给我们之后,我们通过模型算法计算,得出一些农资方面的决策,经销商再问农户要不要,如果要那就交订金,这个量攒到一定规模后,我们可以到市面上找一家厂商定制出来,再由经销商卖给农户,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
是的。有些客户用了我们的技术,收益变高了,他想扩产,但是缺乏资金支持,找到我们寻求帮助,我们因为合作过,对他的地块数据表现很清楚,知道这个人非常可靠,就想帮助他们,慢慢接入了一些金融产品进来。
因为农业金融比较难做,主要是缺乏数据,金融机构没办法详细了解农户的地块种植情况、产量以及历史经营情况,那我们可以帮农户做一个信用报告,供金融机构参考。
不过,金融在我们的收入中占的比例非常小,我们投入的精力很小。目前,我认为在种植端能做的事情非常多,还是要聚焦在帮助老百姓种好地。
相关文章
- “矿二代”弃矿投“田”
- 《留学》一周资讯(613-619)
- 黄平天堂村智慧大棚无土栽培蔬菜
-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朱恩林一行到访丰乐农化
-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2018年种植业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- 2022年有机蔬菜市场行情分析与趋势预测
-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门户网站简介-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- 激活乡村“夜间经济”打造沉浸式乡村
- 关于三农领域的三个好消息你需要知道一下
- 【三农人物】连云港这个村支书登上《新闻联播》!
- “三农”这十年 江西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
- 吉林省启动《中国农业百科全书·吉林卷》编撰工作
- 讲述“三农”故事 交流致富经验 省委农办举办“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”宣讲活动
- 【在知爱建乡村振兴】秦皇台乡邀请泰山学者董合忠教授开展棉花种植技术培训
- 凯里市人民政府现代农业科技
- 抗旱保供水我们在行动④:全市农业灌溉工程更新升级任务提前超额完成
- 句容农业巧打生态牌农业技术与装备
- 白银蒙古族乡积极开展农业统计基础知识培训
-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发布 “十三五”农业科技十项成就
-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一批国家农作物、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